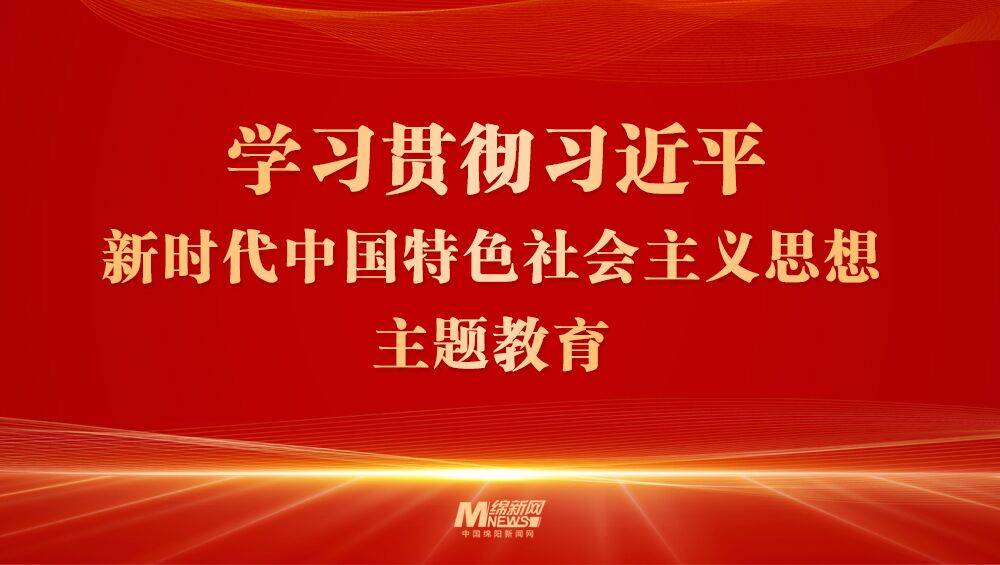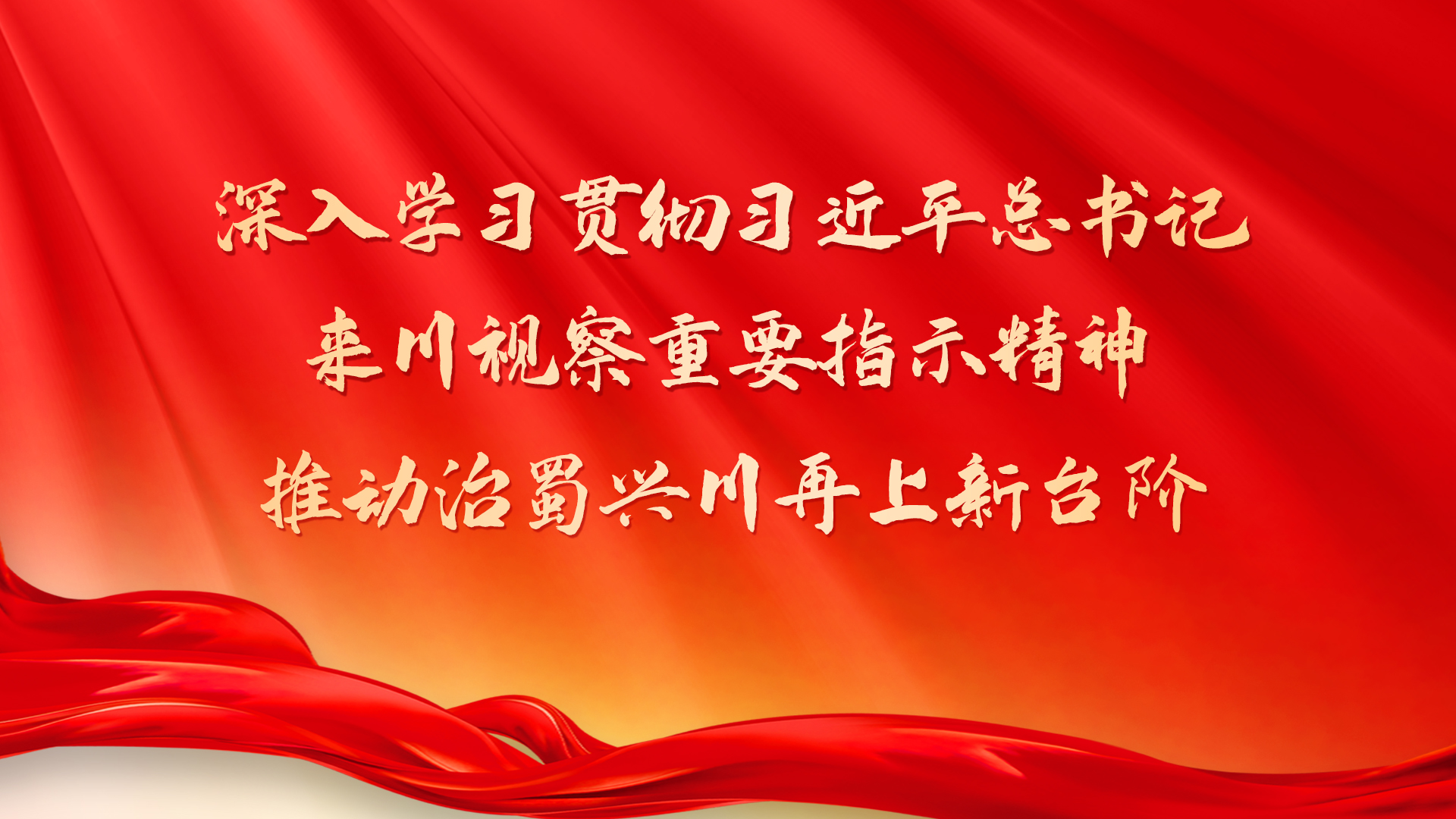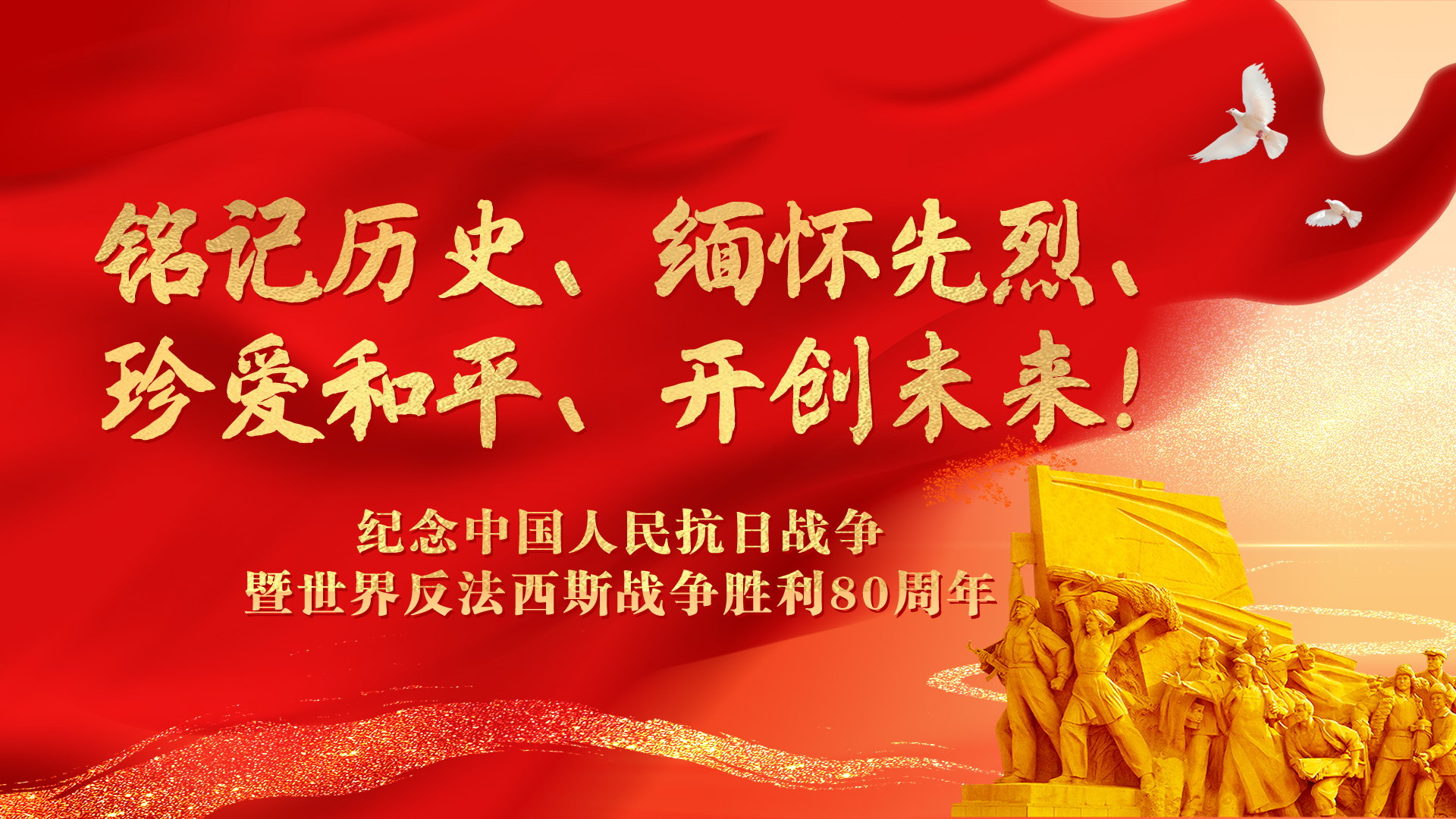□ 黄东速
矗立在我面前的这栋现代建筑叫江油大剧院。它像一个放大了无数倍的火柴盒,坐落在江油县城的东北端。建筑外立面由白黄色砖石构成,正面凹陷约八米,形似巨型蜂窝;右侧一角有现代风格的金黄色半圆形艺术造型,其余部分镶嵌着白色玻璃。在它对面的广场上,立着一块不很起眼的赭红色大理石石碑,上面镌刻着“江油大剧院”。石碑还没到小腿高,不知为何设计得如此小气,总觉得和“江油大剧院”的名字不相称。如今看来,它算不上多么宏伟、艺术的建筑,但在2012年建成时,仍能媲美其他县城的建筑,至少,为这座县城添了几分现代气息。从另一个角度说,它贴合普通县城的身份,像一位时髦又朴实的女子,徘徊在平凡与现代之间。
江油大剧院,很多人都这样称呼,但我不会,我仍叫它改建前的名字——中坝剧场。当别人对我说“江油大剧院”时,我心里会默念一声:“哦,中坝剧场。”其原因,是我见证过它的前世今生——在心里,它早已被时光镀得锃亮。当一个地名与你相伴漫长岁月,便会铭刻在心底,永不生锈。我不知道自己说过多少遍“中坝剧场”,但每说一次,它在心里就多一分光亮,此后再难改口。当我说出“中坝剧场”时,时光仿佛呼啸而来,眼前的大剧院也似轻轻晃动了一下。
中坝剧场始建于1984年,记忆中,它的造型与“江油大剧院”类似,只是少了几分现代艺术感。“5·12”汶川特大地震中,中坝剧场严重受损。2010年10月,作为灾后重建项目,政府投资1.5亿元重建,历时两年完工,命名为江油大剧院。此后,县城的重大活动很多都在这里举行。
中坝剧场的主要功能是放映电影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,看电影是人们最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。那时的县城,放映电影的场所多在中心地带,江油也是如此。中坝剧场成了江油的地标,无人不知,无人不晓。
1984年,我正在长钢技校读书,自然也常常到中坝剧场。
长钢技校位于县城北门外。上学时,我要从长钢生活区穿城而过,若不走纪念碑老路,就走老城外的新路。就在这条新路上,我和青春第一次遇见了中坝剧场。初见时并未太激动,因为厂里也有职工俱乐部放映电影,建筑造型类似,只觉得它或许会占据青春的一部分。
那时,它是城内唯一的影院,看电影是件闪闪发光的事,慰藉着单调的岁月。记得当年发行量最大的杂志是《大众电影》,堪比多年后的《读者》。我在中坝剧场看过《追捕》《佐罗》《庐山恋》《牧马人》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》等影片,许多青春情感都在这里荡漾、呼啸、沸腾。这些电影滋养了我的青春,至今,身体里仍会闪现它们的影子。
那时看电影通常要提前买票。我迈上不高不低的台阶,走到左侧售票窗口。窗口旁贴着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,我特别喜欢看这些海报——它们告诉我,除了县城,还有更广阔的世界。
售票窗口很小,仅能看见售票员的半张脸。印象中,窗口里常坐着一位梳辫子、皮肤白皙的姑娘。我很羡慕她——手里攥着大把电影票。我把钱递进窗口,一双陌生的纤细手伸出来,指尖夹着一张小小的电影票。若是冬天,这双手红肿得像红萝卜,递票时,仿佛也递来了一丝疼痛。后来听说,她去了南方,再也没回县城。
从她手里接过电影票,心里像被塞进了什么,一件快乐又有趣的事,如鸟儿般向我飞来。之后的几天,总会老想着这场电影,它像只小猫在心里挠来挠去,既让人发痒,又让人期待。也有例外,一次因事忘了放映时间,浪费了那张票,当时只觉得像浪费了大半生。最早的电影票才5角,相当于我在技校吃两份喷香的回锅肉。不知从何时起,角票从生活里消失了,像许多逝去的时光。
电影票和角票大小相近,多为白色或蓝色,印着放映时间和座位。对那时的我来说,放映时间就是爆米花爆响的时刻,满是快乐与惊喜。到了放映时间,我来到中坝剧场,在大门口把票交给一位中年男人。他一脸严肃,仿佛秩序的化身——在当时,我觉得他拥有莫大的权力。他低头看了眼票,便放我进去。
进入影院,我按票找座位。若是电影已开场,找座位就有些麻烦。四周一片漆黑,只有一束光穿过黑暗,打在银幕上。眼前是一片乌压压的脑袋,被光束笼罩着,一动不动,全然不顾及着急找座位的人。黑暗中看不清座椅背后的号码,只能慌乱摸索,通常会问问聚精会神的观众,从他们或耐烦或不耐烦的回答中,判断自己的座位。很长一段时间里,影院都是座板可翻动的黄色座椅。我坐在椅子上,把双眼和思绪交给白色银幕,看着别处的世界、别人的故事,青春像子弹般飞向银幕。当片尾字幕升起,灯还未亮,许多人已站起来,座椅翻动的“哗啦啦”声像潮水般响起,似在催促观众离场。
看完电影走出影院,常常觉得天空都不一样了,原本空荡荡的世界和人生,仿佛多了些什么。
技校毕业后,我进了厂。那时厂矿很封闭,我很少进城,去的地方不外乎太白公园和中坝剧场。在中坝剧场,除了看电影,也会喝茶。喝茶的地方就在剧场大门口的走廊上,左侧便是那窄小的售票窗口。有段时间,我常来这里喝茶。把父亲的二八加重永久自行车停在广场左侧角落,迈上台阶,将身体交给一张帆布躺椅,一边喝茶,一边俯瞰广场上或有趣或平淡的场景,看着无用的时光裹着青春慢慢流淌。广场上偶尔有人走过,彼此不相识,却一同沉浮在县城的时光里。有时也会往右边看,稍远处是一片菜畦,不时有老农挥着锄头,他的身影让我想起“劳动”二字。
那时喝的是盖碗茶。每次喝时,我都用指尖捏住白色茶盖,扬一扬甩掉水气,再用茶盖的圆边角拨弄浮在水面的茶花,茶盖不时碰着茶碗,发出轻微而清脆的声音,内心也跟着响动起来。同时,我抿起嘴唇,凑近茶碗,连续呼出几口气,吹动氤氲的澄黄茶水。茶水泛起涟漪,一直波动到这个下午的时光深处。那时总觉得,人世就是一杯茶,世味就是茶味。
如今,在县城里再也找不到盖碗茶了。人们多用没有盖子的粗犷玻璃杯喝茶,常常拎起杯子一扬脖子,茶水便一饮而尽。回想起来,我们丢掉了许多细节之美、萦绕之美、婉约之美,越来越功利和现实——吃饭就是吃饭,喝茶就是喝茶,活着就是活着。
很多个下午,我都在中坝剧场,躺在椅子上喝盖碗茶,陪伴我的,只有天空中的蓝天白云。有时,腰间的摩托罗拉BB机突然颤动,我便起身到剧场左侧的副食店,站在一部黑色电话旁,拿起许多人握过的听筒放在耳边,拨动熟悉的阿拉伯数字,说出那些早已遗忘、消散在风中的话语。
编辑:谭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