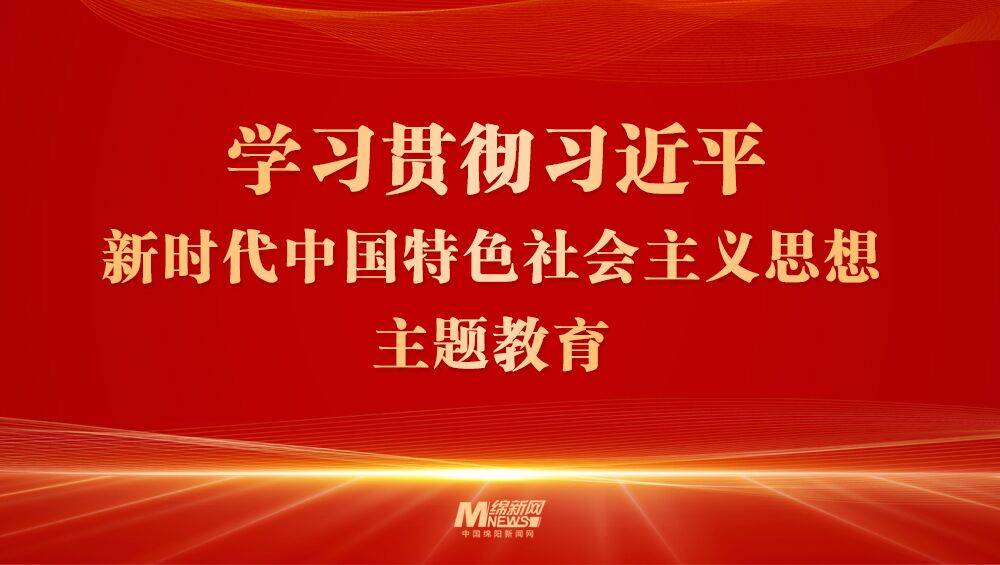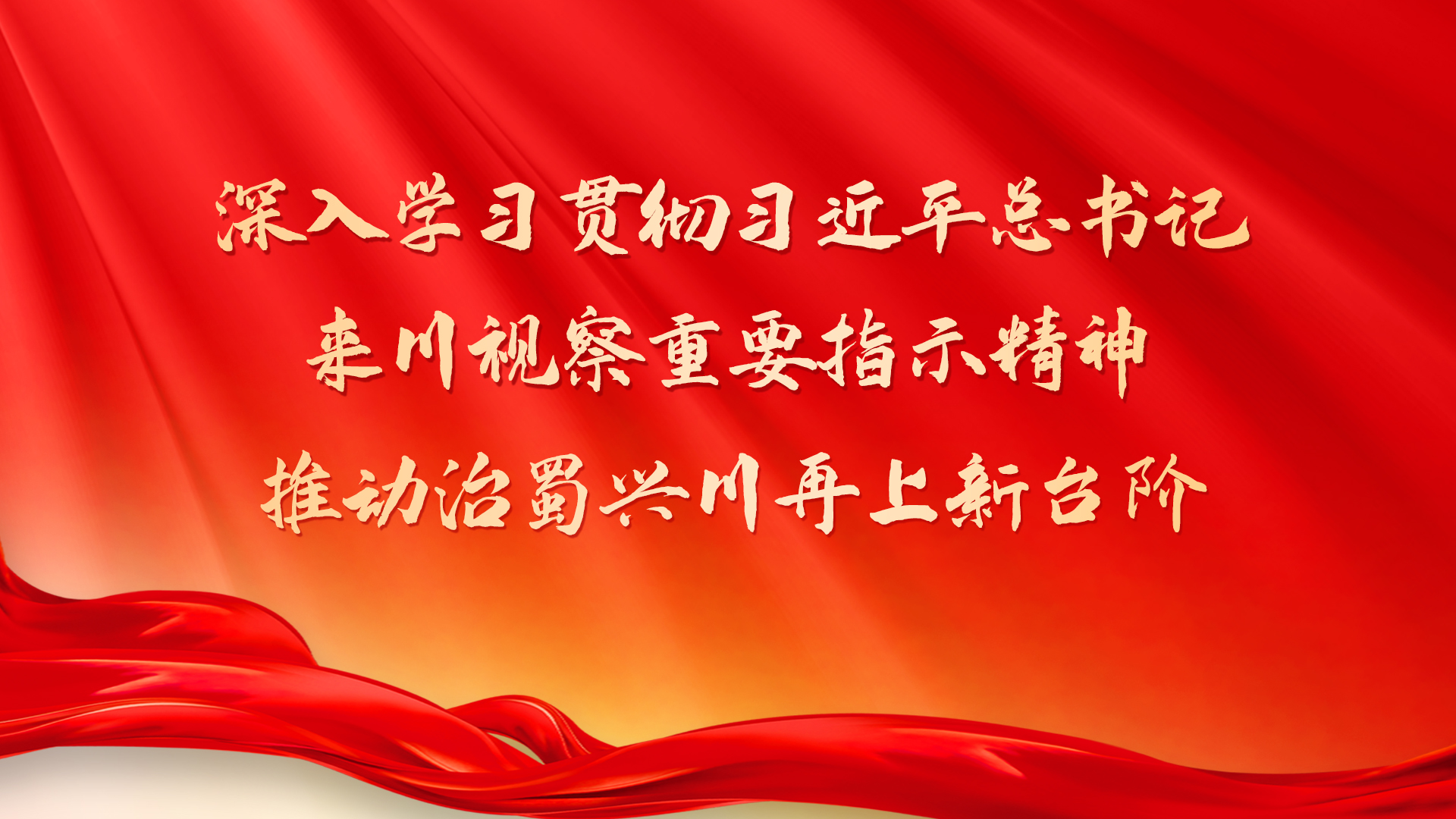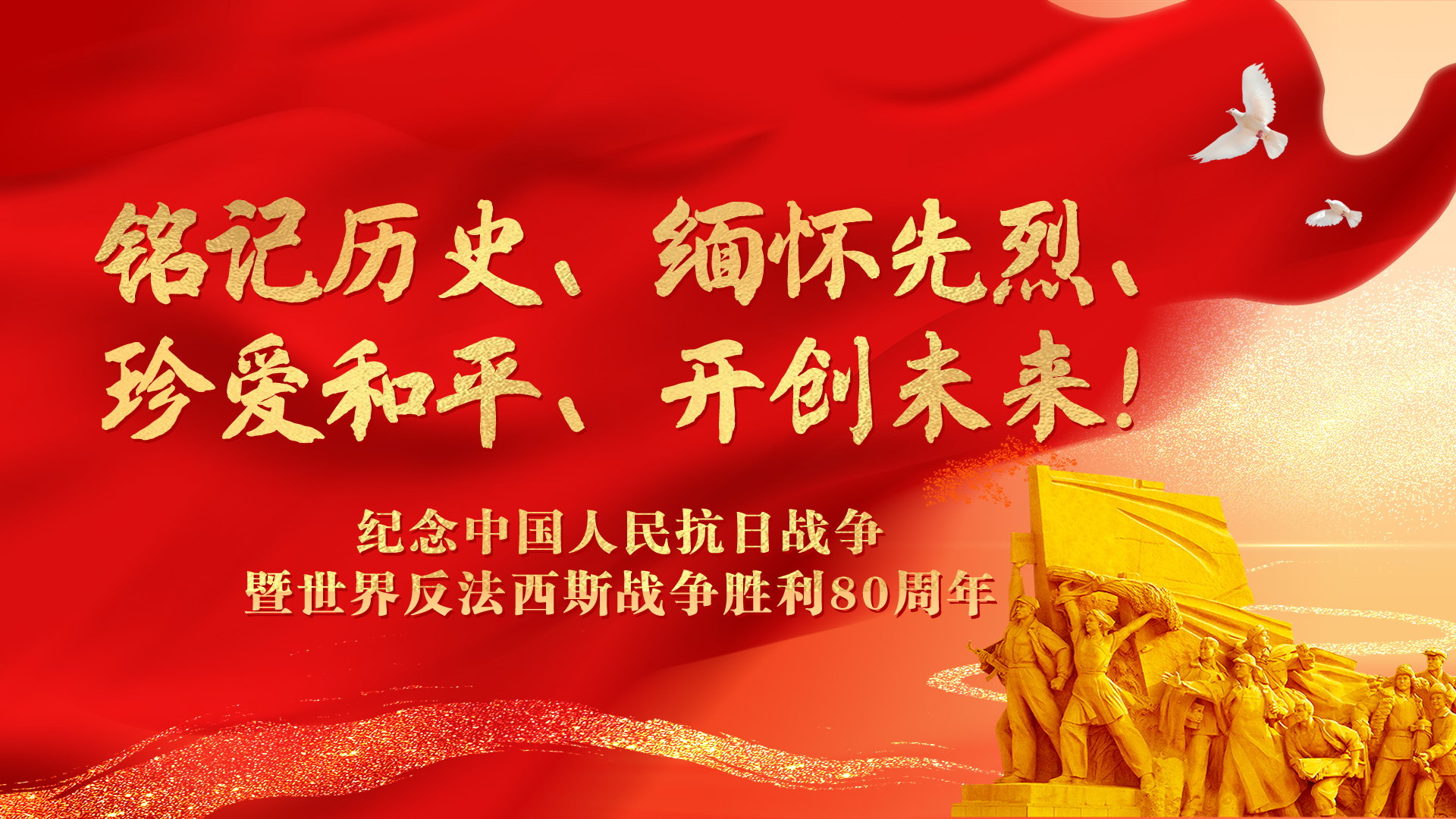□ 杨力
秋日一到,大红的“二荆条”辣椒从田垄间端上了寻常人家的餐桌。不少家庭会采购来做泡椒,而母亲总爱琢磨着做醉椒。
泡椒是用盐水腌的,醉椒则靠白酒浸,用料不同,风味和质感也就有了差别。
家乡在水乡,江河纵横,鱼虾新鲜肥嫩。当地人擅长烹制河鲜,要去鱼腥、提鲜味,泡椒是少不了的。五六斤重的草鱼或花鲢,配上泡椒、泡姜、泡蒜一同烹煮,就是一道让人记挂的家常鱼。这些调味品里,泡椒算是灵魂——它给鱼肉添了鲜辣,又悄悄化解了鱼腥,让普通的食材有了让人惊喜的味道。
醉椒,倒像是泡椒的“升级版”。每年秋天,母亲都会挑一批最饱满的“二荆条”,这些辣椒经历了完整的生长季,又被秋阳多照了些日子,攒足了风味。她把辣椒细细剁碎,“笃笃”的切菜声混着椒香飘出来,是我童年里最熟的秋日声音。碎椒装进坛子,母亲会倒上醇厚的白酒,撒把粗盐,再仔细把坛子封好。接下来的一个月,辣椒就在酒里慢慢发酵,悄悄变着味儿。
小时候总不懂,为啥母亲做的“醉椒鱼”,比别人家的多一分鲜。那辣味不似普通泡椒那样冲,是层层叠叠的醇厚,辣里带香,香完还有点回甘。长大些,母亲才慢慢讲起醉椒的来历。
这手艺,是外曾祖父在漂泊时琢磨出来的。当年水道上热闹,外曾祖父是篷匠,常年在船上过日子。船舱小,生火做饭不方便,他常一次备好几日的饭菜。夏天热,食物容易坏,外曾祖父就想了个法子——把菜装进小坛,撒上盐,再倒些白酒泡着。这样食物能放得久些,里头最常泡的就是红辣椒。
外公小时候最爱去船上看外曾祖父做船篷。到了饭点,外曾祖父总会从坛里拿个醉香的红辣椒,笑着塞给外公。奇的是,白酒泡过的辣椒,没了原来的冲辣,倒有了种特别的醉人香气。用它煮鱼虾、烧豆腐,比寻常调料鲜多了。
外公学会这手艺后,又试着加了花椒、姜蒜这些佐料,让醉椒的味道更丰富了。传了几代人,慢慢改着、完善着,这醉椒成了家里的“独门方子”——辣味柔和,口感又足,做菜时放一点,能把鲜味提得足足的。
醉椒的做法,说到底是微生物在坛里“忙活”。白酒里的酒精挡住了坏菌,盐又帮着调节,好菌就慢慢把辣椒里的蛋白质变成氨基酸,淀粉化成糖,攒出了复杂又顺口的鲜味。
如今在外地,每到秋天,看见市场上红艳艳的辣椒,鼻尖就像飘着醉椒香。那不光是辣椒和白酒混出来的香,是岁月和亲情慢慢酿的味。我知道,那是母亲在老家厨房掀开醉椒坛子呢,是游子心里扯不断的乡愁。
一坛醉椒,装着的不只是辣椒的味,是一家子的记忆,是过日子的智慧,也是对老方法的传承。现在快餐多了,这种要等些日子才好的味道,反倒更稀罕。它像在告诉我们:有些好东西,得等;有些老传统,得传;有些味道记在心里了,就成了一辈子的乡愁。
秋风再起来时,总会想起母亲那坛醉椒——藏在日子里的香,融在血脉里的乡味,还有不管走多远,都有家的呼唤。